以数字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蔡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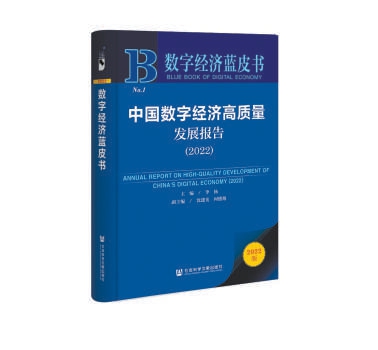
《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报告》 李扬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和京东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围绕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入地合作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并结集出版。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归根结底是整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入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并将无处不在、无远弗届。本书也体现了这个特色,报告作者均为经济学相关领域的专家,分别从税收、债务、金融和融资、反垄断监管、绿色发展,以及促进乡村振兴和智能城市发展等方面,对数字经济以及平台经济进行了深入地研究。
本书是一种集分工与合作、细分与集成、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合作研究成果。不仅这种分工方式和研究过程具有特色,涉及的领域也都是具有最高优先序的,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颇具价值。今后,这种合作研究仍将继续进行。数字经济发展既是提高生产率的必然途径,也应该成为分享生产率的重要领域。借此机会,我拟从提高和分享生产率的角度,简述自己粗浅的思考。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一要求也是指导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准则。从性质上说,数字经济是载体而非目的,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是过程而非终点。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提高和分享生产率的手段,承担着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只有确立这样的功能定位,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数字经济才能获得持续和健康的发展。相应地,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中,数字经济既应该也能够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先从初次分配领域来看。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初次分配是决定生产率提高和分享的基础领域。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合理激励,都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内产生的。分享生产率成果需要以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初次分配领域的激励和效率功能,旨在确保市场主体在竞争中的优胜劣汰,因而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
初次分配也是分享生产率成果的关键领域。研究表明,国家之间在收入差距上的不同表现,并不仅仅在于再分配力度的大小,还产生于初次分配领域在政策取向和制度安排上的差异。这就是说,数字经济发展是否促进生产率分享的导向,并不是产业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因此,若要使数字经济充分发挥生产率分享的作用,进而实现更多更高质量就业岗位创造、劳动者报酬提高以及收入差距缩小等目标,就需要规制和政策有意为之。
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再分配领域的相关制度安排。数字经济提高生产率的作用,最主要来自“熊彼特机制”,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再分配领域的制度安排。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在优胜劣汰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中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过程。
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就是如何使创造性破坏机制既能够发挥提高生产率的作用,又能够发挥分享生产率的作用。这个机制在于,在数字化转型中成功提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扩大自身的同时,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企业遭到淘汰,这就意味着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作用了,整体生产率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提高。如果担心发生技术性失业现象,不敢接受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看似保护了劳动者的利益,实际却因资源重新配置的僵化而阻碍了生产率的提高,分享也就无从谈起。
在尝试回答“索洛悖论”,即为什么广泛采取信息技术却未能提高生产率的疑问时,有研究发现,美国企业的进入率和退出率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整体处于持续降低的态势,使美国经济的营商活力显著降低。生产率提高的停滞意味着做大蛋糕的幅度减弱,分享蛋糕也就成为无米之炊,导致美国社会收入差距的扩大。
不仅如此,无论是在初次分配领域、再分配领域,还是在第三次分配领域,数字化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导向,都可以显著影响生产率的分享程度。提高生产率是市场主体应用数字技术的主要动机,必要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有利于促进生产率的分享。
可以说,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三个分配领域协调配套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通过法律法规、社会规范、舆论引导以及社会诚信体系来营造一个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让各种市场主体自觉地把社会责任具体体现为科技向善、管理向善和创新向善的行动。
(作者为丝绸之路研究院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版权说明: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本网站上的文字、图片、图表、视频等内容。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在相关作品刊发之日起30日内进行。联系方式takefoto@vip.sina.com。

